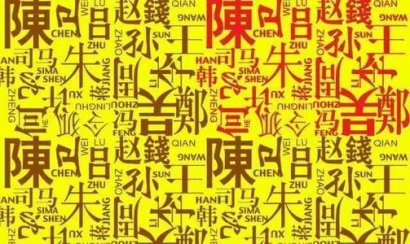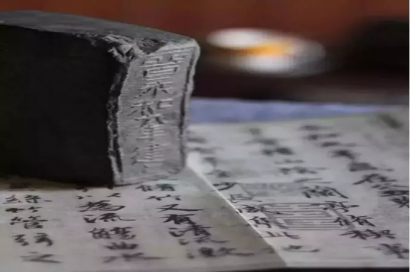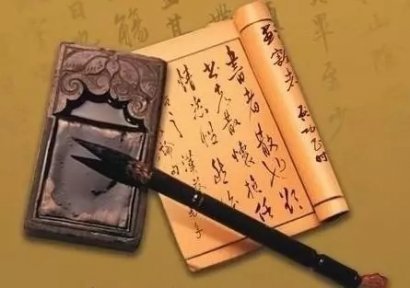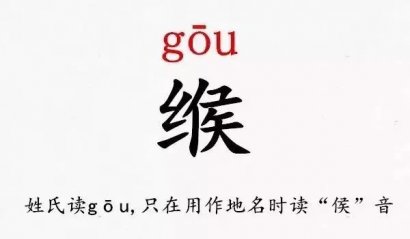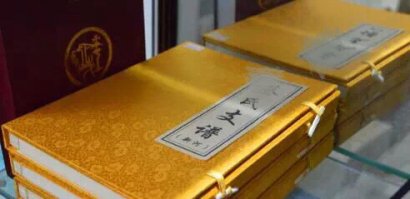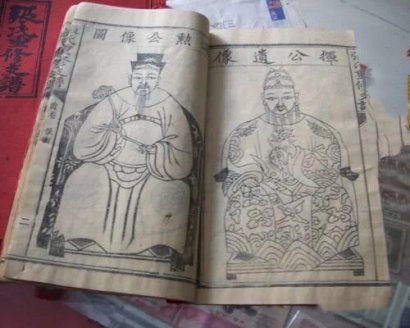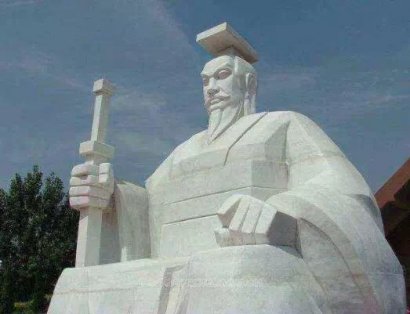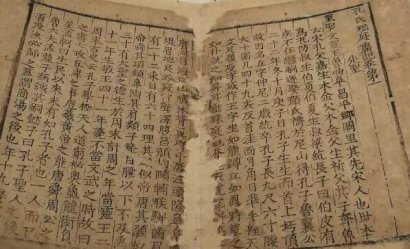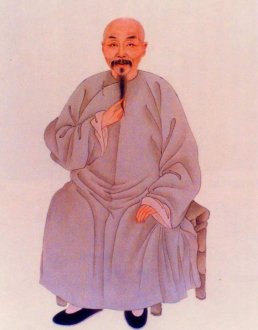敦煌遺書與早期漢藏文化交流
2018-07-23 07:30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作者:朱利華(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伏俊璉(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作為我國文化悠久、影響廣泛的兩大民族,漢、藏之間自古以來就有著密切的文化交流,構成了中華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內容。敦煌遺書中多達上萬件吐蕃統治敦煌地區留下的漢藏文佛教典籍、官私文書、詩文、賬目、雜抄等,真實地呈現了漢藏文化早期交流的具體情形。
唐貞觀八年(634),吐蕃遣使通貢,唐蕃之間的官方交往正式開始。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揭開了唐蕃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深遠影響的一頁。吐蕃開始從服飾、居室、風俗習慣等方面學習唐風,又派遣貴族子弟入朝學習儒家典籍,請漢族文人掌管表疏公文,還“請蠶種及造酒、碾、硙、紙、墨之匠”(《舊唐書·吐蕃傳上》),使唐代工藝文化源源不斷輸入吐蕃本土。景龍四年(710),金城公主出嫁赤德祖贊,“帝念主幼,賜錦繒別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新唐書·吐蕃傳上》),唐蕃文化交流更為密切。
安史之亂爆發后,河西隴右勁旅調往中原平亂,吐蕃趁西北邊防空虛之機大舉進攻唐西北邊境。從廣德二年(764)攻克涼州,到貞元二年(786年)沙州以“毋徙佗境”為約與吐蕃議和,河西走廊進入吐蕃統治時期。大中二年(848),沙州豪強張議潮率眾趕走吐蕃統治者,并于咸通二年(861)收復河西重鎮涼州,河西走廊重新回歸唐朝版圖。吐蕃統治河西諸州的數十年,為漢藏文化的近距離交流提供了一個歷史契機。
吐蕃統治敦煌后,推行了一系列吐蕃化政策,使這些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打破了固有傳統,原有以中原傳統文化為主導的敦煌文化進入了變異期。如軍政職官方面,設立了節度使、乞利本、節兒、監軍、都督等各級官員,改原縣、鄉、里各級行政機構為部落、將,設置部落使、將頭,將吐蕃本土制度與敦煌地區原有唐朝制度進行有機結合。如《陰處士碑》(P.4638)中陰嘉義“所管大蕃瓜州節度行軍先鋒部落上二將告身減旃”,就是唐蕃制度結合的產物。這一時期愿文中有“蕃漢節兒”“二節兒”之稱,說明節兒一職由吐蕃人和漢人共同擔任、分管事務,是吐蕃為了適應新占領地區而制定的新舉措。總體來說,吐蕃在敦煌地區的統治是以合作施政為基礎,為漢藏文化的交流提供了現實保障。
吐蕃統治期間,除吐蕃駐軍外,還有吐蕃僧侶、官吏、百姓移居敦煌地區。由于統治者推行吐蕃文化,敦煌民眾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熊羆愛子,拆襁褓以文身;鴛鴦夫妻,解鬟鈿而辮發。”(P.4640)除“文身”“辮發”外,還要穿吐蕃服飾,這時石窟壁畫中出現了身著吐蕃裝的經變人物形象和供養人像。語言文字方面,漢、藏語并行,涉及軍政、法律、經濟、教育等各個方面。如P.T.1297《寧宗部落夏孜孜永壽寺便麥契》,是用藏文寫成的契約;藏文文書Fr.80匯報沙州驛戶氾國忠等人襲殺蕃官的經過,與漢文文書S.1438中的相關記載一致,是就同一事件向上級匯報的公文。此外,敦煌遺書中保存的《千字文》《開蒙要訓》《九九乘法表》等童蒙讀物,《寒食詩》《孔子項托相問書》《茶酒論》等文學作品,以及《尚書》《戰國策》等傳統典籍都被譯為藏文,供漢人學習藏文或吐蕃人學習漢文化,反映了當時藏文學習和使用的情況。
佛教是包括漢、藏及其他民族在內的敦煌民眾的共同信仰,這一時期的漢藏佛教文化交流最為密切。吐蕃統治者對佛教的大力扶持,既是出于自身信仰的需求,更是在新占領區施政的重要手段。吐蕃統治初期,統治者大興佛教,廣譯真經,延請僧徒入蕃講法,佛教文化交流呈現出一派繁盛景象;吐蕃統治后期,吐蕃僧人法成利用藏漢兩種文字在河西進行翻譯、著述、講經等活動,佛教文化交流更加直接和密切。吐蕃統治者還在敦煌地區組織了大規模的抄經活動,包括漢、藏在內的多個民族的抄經生參與其中,共同致力于藏文佛經的抄寫,其中一些經卷還被送到吐蕃本土寺院收藏至今。可以說,這既是一項聲勢浩大的佛教文化活動,也是一項吐蕃文字的普及活動,更是一項以佛教為共同信仰的民心工程,極大促進了吐蕃佛教與漢地佛教的融合,也促進了敦煌地區以漢藏為主體的多民族文化的交流。
石窟藝術是佛教文化的集中體現。吐蕃統治敦煌之前,敦煌莫高窟已經成為光輝燦爛的佛教藝術殿堂,吐蕃時期在此基礎上繼續修建并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主要體現在:壁畫中出現了吐蕃人物或身著吐蕃服裝的漢人形象。如154窟《金光明最勝王經變》中的趕象人、《藥師經變》中的送食者等都是蕃裝人物。這一時期的《維摩詰經變》與初唐時期同類壁畫有所不同:原本繪制異族番王的位置換成了吐蕃贊普及其侍從的聽法場景,與之相對的則是唐朝皇帝及其侍從。這兩組關鍵人物的相對出現,體現了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畫工的巧妙用意,潛在地表達了敦煌民眾希望唐蕃之間消弭戰爭、維持和平局面的美好愿望。除了繼續使用原有題材外,還增加了《報恩經變》《金光明最勝王經變》等新題材經變畫,其中《金光明最勝王經變》的出現與《金光明最勝王經》在吐蕃統治時期盛行有關,這一題材護世護法的思想主旨,表達了敦煌民眾渴望和平的心愿。在洞窟造型方面也出現了新的因素,如盛唐洞窟已經有少量的屏風畫,到吐蕃統治初期開始增多,至吐蕃統治后期完全成熟,還出現了藏文題記。這些都是漢藏文化交流在石窟藝術中的體現。
文化的嬗變自然會影響文人的心理和創作,使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具有與以往不同的風貌。這一時期的漢文文學不僅體現漢民族的文化心理,也間接反映了吐蕃統治者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古藏文作品是該時期文學的新因素,集中體現了漢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陷蕃初期以“陷蕃詩”為代表的作品,無不充溢著“破落官”“沒落官”的故國之思。吐蕃統治中后期,僧俗文人為吐蕃統治者撰寫功德記,并在佛事應用文中為其祈福禳災,體現了文人心態的變化和文學的變異。
在推行吐蕃化管理的同時,吐蕃統治者和民眾也在大量學習、接受漢文化。吐蕃官員在沙州修建寺院,并請漢族文人撰寫功德記。如敦煌文人竇良驥撰寫的《尚起律心兒圣光寺功德頌》,是沙州首任守官尚綺心兒修建圣光寺的功德記,《吐蕃論董勃藏修伽藍功德記》是吐蕃官員董勃藏修建敦煌“州東三里平河口側,故壞伽藍一所”的功德記。功德記中歷述家世淵源、本人生平事跡,與漢人功德記并無二致。又如藏文本《禮儀問答寫本》,以對話形式論述待人接物,應對進退,處理君臣、父子、師生和主仆乃至夫妻之間的關系,體現了對儒家思想中“忠孝”這一核心文化的吸收。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是有關吐蕃早期歷史的第一手資料,包括吐蕃大事紀年、吐蕃贊普傳記、小邦邦伯家臣及贊普事跡三部分,是吐蕃受到敦煌漢族士人重史、修史之風直接影響的具體體現。這些吐蕃歷史文獻產生于7至10世紀,幾乎從藏文的創制開始,直到9世紀中葉吐蕃統治者退出河西地區以后仍在繼續,對后世了解吐蕃早期歷史文化及漢藏文化的早期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光明日報》( 2018年07月23日 13版)
[責任編輯:張悅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