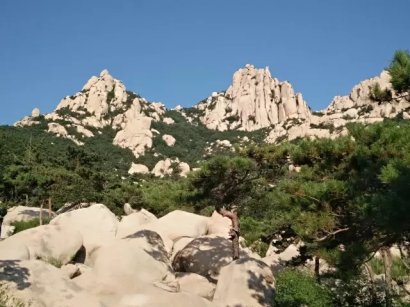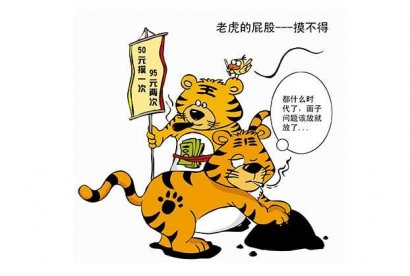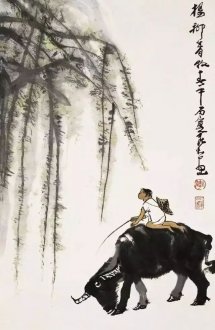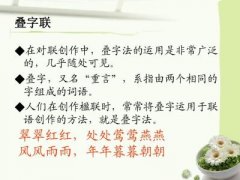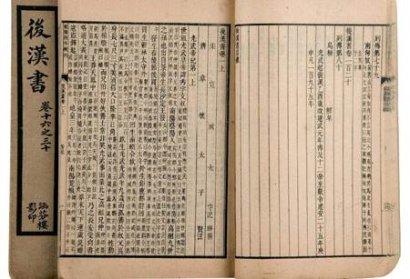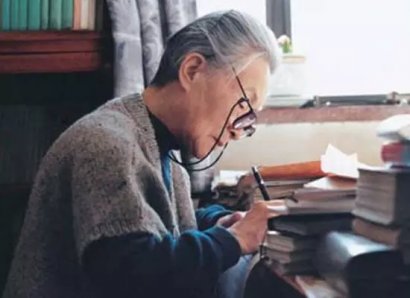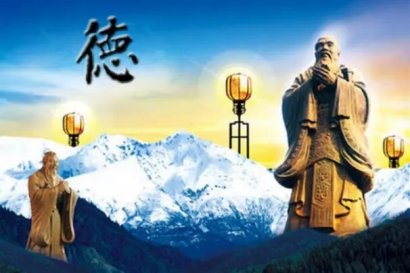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法治國的大時代
作者:皮家嶺的哥 來源:我們愛歷史
有人說中國自古缺乏法治精神。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近來學史,略有一些粗淺的認識:中國古代的法家注重實踐,忽略了理論,沒有形成像西方那樣嚴密的法理系統,法家思想在歷史精英的治國理政實踐中體現出來,而儒家思想的理論體系則十分完善,門徒眾多,宣傳得十分到位,形成整個社會的主流輿論場。追溯法家思想的起源,可以從管仲說起。管仲相齊,推行大膽變革,主張嚴肅法紀,“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他的改革幫助齊國實現強盛,“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一霸。管仲之后,晉國效仿齊國改革,并“鑄刑鼎”向民眾公布法令,開啟了“明法”的先河,成為中國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法治事件都是在改革實踐中推行,并沒有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而真正將法治變為一種思想,并在改革中踐行的,是三家分晉之后的魏國李悝。
李悝在魏國實行變法,主張廢止 世襲貴族 特權,提出“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制定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法經》。魏國因李悝變法成為戰國初期第一個強國。與此同時,吳起在楚國變法,變法的內容與李悝差不多。后來,商鞅、申不害又分別在秦國、韓國推行變法,也是以法治為主要內容,分別造就了這些國家強盛一時、稱雄一方。
按照史學家的觀點,春秋戰國是西周禮制崩壞的階段,“以禮治國”的思想基礎逐漸瓦解,于是形成諸子百家思想爭鳴的熱鬧景象。但是,熱鬧之中細細品味,不過是“人治”與“法治”的爭鋒,或者說是“以德治國”與“以法治國”思想的交鋒。這其中與社會關懷最為密切,同時又直接干系到治國興邦的,則主要是儒法兩家的思想。
孔子是周公的信徒,儒家的主張是恢復禮制,“為中華人提出一個美麗的回顧――而不是一個美麗的前瞻”(柏楊),試圖在舊有的社會等級制度體系上建立一個“仁政”系統,以“仁者愛人”的思想作基礎建立一套“德治”的治國方略。儒家抱定悲天憫人的社會關懷情結,所以信眾甚廣,加之孔子善于宣傳、善于教化,使儒家思想到戰國時期已經形成了十分完備的思想體系。但是,不論孔子還是他的繼承者們,在政治生涯上卻是失敗的,它們的思想雖然影響到后世的整個教育,卻并沒有成為諸侯們安邦定國的“基本國策”。在戰國時期,孟子以“仁義”思想游說列國,希望能用“仁政”教化天下,但是諸侯 們表面上都很客氣,都說儒家的思想好,卻沒有一個愿意將“仁政”付諸實踐,實際上是沒人理會的。
法家思想也是對崩壞的“禮制”進行重構的思想體系,但是它不是恢復,而是重建,與禮制的層層等級不一樣,法家要建立的是以“君-法”為基礎的新制度體系,雖然沒有脫離“人治”的本質,但是開始實現了“法治”思想與“人治”的結合。李悝、商鞅乃至后來的韓非子,先后從理論上對法治思想進行了闡述,但是與儒家的理論相比,法的思想總結得是不夠的,尤其在法理和法的精神上并沒有作過多的提煉,法學家們也沒有像孔孟一樣,有那么多的弟子門徒四出宣揚,所以法家思想更多體現在實踐層面。
實際上,戰國諸侯們都在踐行法治思想,只是六國的法治改革未能徹底,惟有秦國從商鞅到范雎、李斯,一以貫之地推行法治化改革,使秦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越來越強大,并最終實現一統天下的大業。
所以,秦國的勝利,說到底就是法治的勝利。
徒木立信:法治精神的第一個標桿
“商鞅變法”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可以說是二千年封建制度的濫觴,也是最早的一次大規模土地革命。商鞅主政變法二十年之久,以法治國,奠定了秦國強大的基石。據說毛澤東曾這樣評價:“商鞅首屈一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是一個具有宗教徒般篤誠和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商鞅之法懲奸究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福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貪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商鞅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徹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僅限于當時,更影響了中國數千年。”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思想影響甚深。魏國國相公孫痤臨終前向魏惠王舉薦公孫鞅,但并沒有引起惠王的重視。當秦、楚還只是不被中原諸國看得起的蠻夷不開化民族之時,魏國就已經是黃河中游地區最強大的國家之一。但是,強大的魏國卻在用人問題上一再犯錯,先是容不下吳起,后來又容不下孫臏,這一次又沒有認識到商鞅的才干,錯失了可能成為諸侯國中最強者的機遇。
商鞅懷揣李悝的《法經》到了秦國,得到了秦孝公的賞識,開始實施變法,用法治的制度體系取代舊有的等級制度體系,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也完成了一次具有歷史性意義的變革。
商鞅變法的內容包括:廢井田、開阡陌,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統一度量衡,廢除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等等,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等各個方面。而其治國理政的核心思想是“任法而治”,認為安邦定國“不可以須臾忘于法”。他的法治思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舉張因時而易制定法度,而不能泥法過去的禮制,“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禮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二是推行法令必須“刑無等級”,認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所以執法要不避權貴,刑也可以上大夫,這是法家思想的一個關鍵,即在國君以下,人人在法面前都是平等的。三是“明法”,即讓百姓知曉法律、遵循法律,“王者刑賞斷于民心”,讓老百姓知道什么是可為的、什么是不可為的,“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
商鞅要推動變法,但是擔心天下人對新法沒有信心,于是樹起了確立中國古代法治精神的第一座標桿:徙木立信。
他在都市南門外放一根三丈之木于,宣稱誰能將它移到北門,賞十金。百姓覺得這事兒很不靠譜,所以并沒有人理會。于是商鞅再下令,將獎賞提高到五十金。于是就有個人斗膽一試了,將木頭從南門搬到了北門。商鞅立即兌現, “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有了這一序曲,后面的改革大戲就好上演多了。這可謂是為新法施行作了一次生動的宣傳造勢。
“徙木立信”的意義在于讓老百姓知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道理,而商鞅在改革過程也堅定地貫徹了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治理念。太子駟觸犯新法,商鞅說,太子是君嗣,不可施刑,但是那是因為教導太子的老師沒有教好,所以必須承擔這個責任,于是以重刑處罰太子之師公子虔,以黥刑處罰另一位老師公孫賈,就是在他臉上刺字。這是對權貴的挑戰,改變了刑不上大夫的舊例,法治思想從此為民所接受,“明日,秦人皆趨令”。
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成效十分顯著。戰國初期,秦國一直是“七雄”之中“最不雄”的一個,直至商鞅變法以后,才以軍事強悍、法紀嚴明、國力雄厚的形象,無敵于天下,成為七雄之首。
當然,商鞅也因為刑法過于嚴酷、輕罪重處、冷血無情而受到后世的指斥,這對于以“人治”為基礎的獨尊儒術的后世統治思想來說,更是不可寬恕,連司馬遷也說他“天資刻薄”。賈誼則說“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不知賈先生怎么看到的是日益強大的秦國“俗日敗”了?
商鞅的結局是悲劇式的,在孝公死后,太子繼位,第一件事就是把這個曾經嚴懲了自己老師的人給族誅了。但是,商鞅的治國之策并沒有被廢,他的法治方略一直被沿用。以至數十年之后,荀子所看到的秦國已經是一個“恬然如無治”的國家了:“國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淫蕩)汙(猥褻),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順。……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入其國,觀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觀其朝廷,其朝(早)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張蔭麟《中國史綱》)
韓非的理論與李斯的實踐
荀子的兩個門徒成就了秦始皇的霸業,一個是韓非子,一個是李斯。他們一個是法治思想的集大成者,是理論家;一個是法治政策的推行者,是實踐家。秦王贏政信奉韓非子的理論,而重用李斯推行進一步的改革和擴張。
《 史記 》記載,韓非子精于“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韓非子雖然是荀子的弟子,但卻沒有承襲荀子的儒家思想(實際上,荀子的儒家思想中已經透出了法治的思想痕跡),而對李悝、商鞅、申不害等法家的思想進行總結完善,建立了一個“以法為本”、“法勢術”三者結合的思想體系。他的思想基礎與荀子一樣,是“性惡論”者,認為民眾的本性是“惡勞而好逸”,但是荀子認為可以通過仁德的教化“化性起偽”,改變民眾的本性,而韓非則認為只有以法來約束民眾,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為萌”。在治國的方略上,韓非提出了法、勢、術相結合的法治理論,以法為本,結合勢術,法是指法令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勢是人主的威權,獨掌大權的威勢,術則是駕御群臣、操縱朝堂的謀略和手段。可以看出,韓非子總結了一套實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論,卻在法治精神的本義上并沒有太多的建樹,重在對君權的指導,更缺乏對人性的關懷,大概這就是其理論不能像儒家思想一樣系統性地為公眾所接受的原因吧。
秦始皇十分欣賞這個韓國公子的學術思想,甚至對眾人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意即能夠與他見上一面,高談闊論一番,死而無憾。然而他們見面之后,死的卻是韓非,他的同門師兄弟李斯把他給害死了。史學家們認為李斯誣陷謗殺韓非,原因是嫉妒他的才能、擔心自己宰相地位不保。但我想,作為一個敵國的公子有如此高的政治才能和學術造詣,深得法家思想要義的李斯,是不可能留下他,讓他成為本國一統天下的障礙。韓非子死后,他的那本代表法家思想總成的《韓非子》成了緊俏貨,各國國君和大臣競相研讀,秦始皇更是將其奉為圣典,在法、勢、術思想指引下,完成霸業。
李斯也是法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沒有韓非子那么深厚的理論造詣,但是他卻在秦國決戰決勝的關鍵時刻,實踐著法家思想,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遠見,輔助贏政完成宏圖大業。李斯沿襲了商鞅的變革舉措,并在政治結構改革、經濟結構改革方面都更進一步,實行郡縣制,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統一文字,以法治的思想為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搭起了總體框架,使后世二千余年的國家治理有了一個基本格局。
司馬遷評價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 六藝 》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茍合, 嚴威 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 俗議 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那意思是他的功勞本來是很高的,其至可以與周公、召公相媲美,可惜他憑仗顯貴的地位,阿諛奉承、隨意附合、酷刑峻法、聽信邪說,廢掉嫡子扶蘇而立庶子胡亥,等到各地群起反叛,想要勸諫卻為時已晚,將自己的歷史功績抹殺了一大半,還召至腰斬之禍。
韓非和李斯,分別從理論和實踐上影響贏政,改變秦國,并決定了中國的未來走向,這是法治思想在諸子百家的爭鳴中取得最終勝利。但是,秦帝國的命運并不長,酷刑峻法、橫征暴斂的“暴政”使其僅存十五年就走向覆亡,成為歷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實在是成也法家,敗也法家。
說它敗也法家,是因為李斯等人在后期將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極端化,這種極端化在商鞅時期就已經有所顯露。在“以法治國”還是“以德治國”的問題上,他們都是只信“法”而不信“德”的。一個典型的事件就是“焚書坑儒”。商鞅時期就曾燒詩書、禁游學,秦統一六國后,統治者和幕僚們以為憑法家得天下,那么治天下用法家就可以了,其他的思想都是“偽思想”,不必要存在,留著他們只會召至“入則心非,出則巷議”,所以不如一并鏟除。秦亡以后,法家的思想一直未能進入中國傳統思想的主流,一方面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壟斷地位更迎合封建皇權和仕大夫階層的利益訴求,另一方面也因為商鞅、李斯等人在法治思想上過“左”的路線所造成。
關鍵詞: 法家
本文來源于古典文學網(www.gdwxcn.com),轉載請保留原文鏈接及注明出處。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